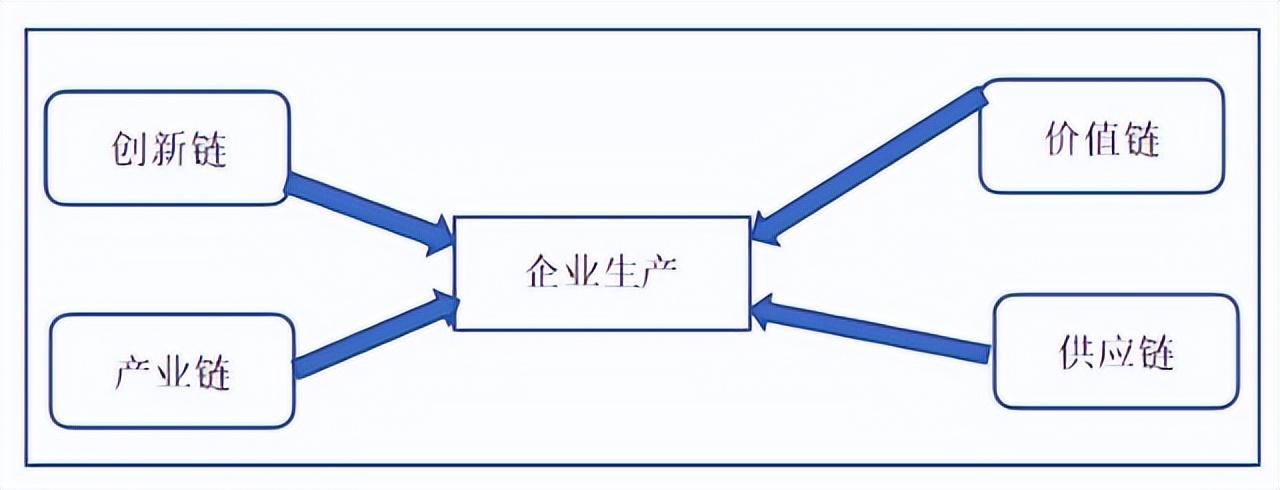“花了那么多钱培养你,好不容易在公立医院当了医生,突然之间,铁饭碗说不要就不要了?”这样的质疑曾经出现在几乎每一个从公立医院走到民营医院的医生面前。
尽管目前在微博上已经拥有超过150万粉丝,在知乎拥有超过20万粉丝,还曾经登上过湖南卫视《天天向上》的舞台,供职于头部毛发医疗机构雍禾医疗,作为毛发医生执业10年,做过近万台植发手术,但回忆起自己来到民营医疗机构的经历,徐鲁依然记忆犹新。
雍禾医疗植发医生徐鲁
21世纪10年代,山东菏泽的普外科医生徐鲁正挣扎在属于自己的命运旋涡里。
徐鲁属于最先嗅到机遇的那批人。
2002年FDA(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Botox(保妥适)治疗眉间皱纹。一向严谨异常的FDA破天荒地批准一种纯粹用于美容目的的药物上市销售。这标志着消费医疗与医疗美容在美国的快速兴起。
在2001年我国加入WTO后,陆续引进了国外的医疗美容先进理念和技术,国内医疗美容行业与国民的医疗美容意识都在快速发展。
早先在青岛就读临床医学的徐鲁最先感知到医美的影响,由于地域与历史因素影响,青岛吸引了大量日韩企业的投资,而彼时“韩风”凛冽下,青岛、大连等地区也流行起去韩国进行医美手术的风潮,据资料显示,中国赴韩整形人数从2010年的0.2万人次增长至2014年的5.6万人次,5年增长近30倍。
与医疗美容、消费医疗一起发展起来的民营医疗机构为“医生”这个职业提供了可以快速成长的发展空间。“在民营医院,大家肯定都在指望你。”徐鲁回忆起刚来雍禾植发时的情景时说:“这种环境会逼着你快速成长。”
包括徐鲁、王传凯李建新与侯媛在内的众多医生看到了职业生涯的另一种可能,但改变从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出奔
他(她)们要从原有的体系中出奔,奔到光芒发出来的地方去,去建设一个全新的体系。
理想光芒万丈,现实冷若冰霜。砸掉“铁饭碗”不仅需要勇气,更是要面对来自于家庭、社会的压力。
这种观念根深蒂固到做了毛发医生四五年之后,来到民营医疗机构是否正确的念头依然会从某个不知名的犄角旮旯里冒出来,在山东菏泽人王传凯的内心深处晃荡一圈。
同为菏泽人的徐鲁则选择直接回避这个尖锐的矛盾:“不敢跟我爸说。”他与妻子“合谋”给自己找了个光鲜的借口:去北京进修。
身处北京的侯媛对于这场大时代背景下的“出奔”倒没有感受到压力山大,甚至感觉有点庆幸:“算是遇到贵人了。”她的前领导介绍她去做一名植发医生。

雍禾医疗植发医生李建新
能遇到“贵人”的几率并不高,大多数人依然要奔着那有光处,鼓足勇气猛冲过去。同在北京的李建新就不得不在连妻子都不理解他的选择的情况下毅然奔向民营医疗机构,“撞”出个未来。
沉寂
激情如火的出奔之后并不是一次灿若烟火的爆发,而是以年为单位的沉寂。
沉寂首先来自于雍禾植发对于医生的培训要求,即便是手持“医师资格证书”和“医师执业证书”的医生来到雍禾植发也要经过培训。
“你来了以后在我这学六个月,六个月你学不成,我也不能再用你了,说明你不适合做植发。”来到雍禾植发,首先拦在徐鲁、王传凯、李建新、侯媛们面前的就是雍禾植发创始人张玉开诚布公地设下的“拦路虎”。

植发医生侯媛
即便是在植发这个行业执业多年,侯媛2017年来到雍禾植发依然结结实实坐了回冷板凳:“那几个月,除了熟悉雍禾的手术流程,就是天天练习打孔,每天从医务那里领五张打孔的单子,坐在那练习,基本上就是一练一整天。”
让这些医生沉寂的除了长时间的再度学习训练,还源于患者更慢的反馈。
作为一个曾经的手外科医生,王传凯习惯的治疗模式是在显微镜下接上纤细的血管与神经线,手术完成的那一刹那,患者的手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心里已经有数,患者在从麻醉中醒来后,就会满怀对于主刀大夫的感激之情。身处菏泽这个木材加工基地,面对的是“十个木工九断指”的木材产业工人,王传凯原本已经习惯了鲁西南地区木材工人质朴而热烈的正向反馈。
植发则完全不同。从植发到头发长出来并初具规模,往往需要半年以上的时间,半年这个时间节点也并非终点,“五年后种植的头发还好不好,十年后头发还好不好?”植发医生必须经历更挑剔的审视与更长久的等待。
更长久的等待并不意味着未来的一定更灿烂,在毛发行业发展的历程中,大量医生耐不住寂寞,选择黯然离场。毛发医生们的等待就像还未长出头发的毛囊,你以为它在努力吸取营养,等待茁壮成长,他/她已经在长久的沉寂中选择了离开战场。
成长
沉寂难捱,但对于有心者而言,沉寂的时间不会虚度。
2008年,作为行业先行者,雍禾从美国率先引进FUE植发技术。
2010年,雍禾植发制定了植发行业标准,获得央视报道。在雍禾植发的引导下,FUE这种伤害更小的植发手术在迅速获得植发患者认可的同时,也让雍禾植发规模迅速扩张。
“相对而言,FUT技术手术毛囊成活率更高,因为它是整块皮肤剥离后,再将皮肤组织分离成带着脂肪组织,包裹着毛囊,适应移植部位形状的皮瓣进行种植,但是由于FUT手术过程中,要对皮肤进行拉伸,FUT手术有可能伤及神经,它的后遗症之一就是头疼,恢复期过后,依然可能有头疼的症状,相对而言,FUE手术伤害更小,恢复更快,而只要医生取毛囊的手法足够熟练,取毛囊的时候不伤害毛囊,种植的速度也够快,毛囊的成活率是有保障的。”侯媛见证了FUE技术对FUT技术的快速迭代。
而徐鲁、李建新、王传凯这批在2010年前后加入雍禾植发的医生成了FUE技术与中国植发行业快速发展的见证者与推动者,也是获益者。
相较FUT技术,FUE技术看起来降低了手术操作的门槛,实际上对于医生的熟练程度、种植速度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见过执业5年的植发医生,做一台种植量大的手术,做到一半,做不下去了。”王传凯说:“后枕部供区是植发手术的‘种苗基地’,做一台种植量大的手术,如果你技术不过关,打孔七歪八扭,手术做到一半,你就把供区资源破坏殆尽了,在供区提取不出来可以种植的毛囊了,那你还怎么做?”
FUE技术让植发成了一个“门槛在门里”的行业,爱听郭德纲相声的王传凯对这点深有体会,在这道隐形的门槛影响下,雍禾植发的医生们自然有了去成为“好医生”的自觉,而“好医生”也在推动毛发医疗行业“好制度”的诞生与完善。

李建新为患者诊疗
李建新对自己多年前做过的一台植发手术印象记忆犹新。2015年前后,一位来自大连的母亲带着自己的孩子来做植发手术,“那时候,我们做手术的盘子里一边放着待种植的毛囊,一边放着手术中用过的种植针。”手术完毕,使用过的一次性种植针自然被扔进了垃圾桶,谁料这一举动让这位母亲在院部大吵大闹:“她一直通过直播看我们手术的现场,看到我们把植发针扔了,误认为植发针是我们提取的毛囊没有种植完,直接扔了。”
自认为手术做得不错的李建新深受打击,这次手术过后,在李建新的推动和倡议下,雍禾植发对手术流程进行了改进与规范:植发前,要跟患者清点清楚种植毛囊的数量,种植后,要把已经种植完毕的空盘展示给患者,并告知种植的具体情况。就是在这样的一次次碰撞中,医生、雍禾植发、植发行业都在快速成长。
制度与流程的完善带来的好处显而易见。“医生可能出错,制度不会出错。”侯媛说:“医生是人,人就是会犯错误的,几率再小,也会犯错,但是雍禾主导下不断完善的制度与流程保障了医生不会犯错,或者即便犯错了,也可以经由制度补救。”
超越
在雍禾,在沉寂中成长起来的“好医生”们正在追求对于“医生”这一传统角色的超越。
“你看这是我打的孔,前三四排稀疏松散,后边比较密。你看,比较规整,它的方向角度是扇形铺开,就是左边朝左边,右边朝右边,中间朝中间,然后(每个种植孔)角度大概45度角左右。”初次见面,侯媛就可以热络地拿出接受自己毛囊移植手术患者的打孔图片与人分享,她尽量把自己的身体斜斜伸直,以便将手中颇有些血腥的照片以最佳的角度和距离展示出来,并铺开手掌,以便别人理解扇形铺开到底是如何铺开。
“爱分享”的侯媛曾吓到过自己的闺蜜,让她赶紧把手机拿开,“你看看嘛,毛囊像一个小宝宝似的,多可爱啊。”

侯媛为女性患者诊疗
在侯媛看来,民营机构的医生尤其是毛发医生,有机会做得更好。“普通医生高强度的工作会磨灭掉医生对病人的共情能力。”侯媛说:“植发医生不一样,取毛囊,几小时,种植几小时,这么长的时间,医生跟病人不能不聊天,植发医生很容易跟病人共情。”
“如果躺在病床上的是我,那我会怎么样?”共情能力让侯媛选择做个更好的医生:“慢下来,我一天比别人少做一台手术,取毛囊取得更细,种植种得更精,患者痛苦更少,种植效果更好。”
近几年,侯媛还在雍禾植发推动了用小针施行麻醉的改革,侯媛在手术中见过很多在麻醉时喊疼的患者:“头皮神经还是比较敏感的,用大针打麻醉当然快,但是也更疼。”在侯媛的建议下,雍禾植发创始人张玉为侯媛买进了专门打麻醉的小针:“一盒一百支,一千块,我打一次麻醉就要用掉10支。”成本更高的小针麻醉在张玉的支持下在雍禾内部快速推广:“这也是我愿意留在雍禾的原因,张总是真的愿意为患者好。”现在侯媛在院部看到年轻医生开始用小针做麻醉,经常不自觉地泛起“姨母笑”:“他们也不知道我在笑什么,估计会感觉我有点怪怪的。”
而徐鲁、王传凯则试图在毛发医疗行业重塑“医生”的形象。持续困扰毛发医生们的问题之一就是尽管他们一直是医生,却往往不被人当做医生。“患者来到民营医疗机构,感觉就是来和你做生意的。”徐鲁说:“我是医生,那么患者要听我的医嘱,如果患者当我是做生意的,那我与患者之间就只剩下讨价还价了。”价可以侃,治疗方案也可以讨价还价:“我说这个药一天要抹两次,你问我两天抹一次是不是也行?”
“真诚反而能打动人。”面对患者的认知错位,王传凯的解决方案是抛弃套路,把一切疑虑和问题都放在桌面上解决:“咱们患者大部分是男士,成功人士居多,都是高智商人士,你去过度包装反而不好,包装太多,他反而会怀疑你。”在王传凯这里,没有什么是不能摊开揉碎说清楚的,这反倒让他获得了患者的信任。

徐鲁在为病人进行诊疗
而为了重塑毛发医疗行业医生群体的形象,徐鲁甚至为自己找了个“偶像”:“姜振宇你知道吧?《非常了得》的嘉宾,微反应微表情的专家。我就经常听他说话,看他在沟通交流时候的表情。”
在徐鲁看来,自己的声音太绵,“我爷爷就说我的声音不着实,说出来的话让人没有信任感。”为了让自己的声音更容易获得信任,徐鲁有意识地训练自己说话:“训练自己的语速,说话重音落在哪里,我经常对着自己的微信号发语音,然后听自己的说话,是不是可信,有没有重点。”
除了声音,徐鲁还要求自己与患者交流的时候眼神笃定,说话的时候放松,微微带笑“当然你也不能一直盯着患者看,把人家看毛了,但是说关键的话的时候一定要盯着患者。”
作为雍禾植发等级最高的医生“雍享院长”之一,徐鲁经常在想的是“如何匹配这个位置”。医生的形象就是他希望解决的问题之一,不仅因为在民营医疗机构,“医生很容易被患者捏着走”,更是因为没有患者心目中的医生形象与医生价值感,就无法真正谈及疗效:“患者一直怀疑你,你还怎么治疗?”

植发医生王传凯
作为毛发医生,雍禾医生们希望做到的还有更多,比如通过毛发的诊疗改变容貌甚至改变人生。王传凯接诊过一个烧伤的患者:“不敢见人,天天出门就戴帽子戴假发,不自信,跟谁都不交流,跟父母都不说话,连一个朋友都没有,完全不会跟你对视。”王传凯甚至怀疑这位患者是不是因为自闭已经造成语言系统退化了。植发手术一年后,这位患者再度拜访王传凯,一进门就主动给王传凯鞠躬,打招呼,描述自己状况的改善:“有个成语就是茅塞顿开,用在这里可能不恰当,但是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个患者突然开窍了。”
正是这样的从容貌到心理的治愈让毛发医生能够在忙到爆的工作中支撑下来。“植发给人能带来特别的有意义的东西,你说是吧?”王传凯说:“不会说把你自己干抑郁了。”
抑郁可能有些言重,但是在目前,毛发医生们确实需要更多地改变自己的生活。

2021年-2022年,尽管疫情肆虐,徐鲁的飞行路线依然在地图上划出了一朵跨越14万公里,盛放的“花”。
“医生比患者的病还多。”徐鲁这样自嘲,一周7天辗转7个城市,做10台手术,只因为航班延误在床上睡过一晚,其余时间都不得不在飞机或高铁上入睡,这样的经历对于徐鲁并不罕见。李建新在经历了三年疫情之后依然保留着隔几分钟看一次手机,患者有需求,就必须拎着早就在办公室准备好的箱子,马上出发的紧绷状态。有限的雍禾“好医生”难以满足喷涌的植发需求。
“很多人问我当医生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也没有那么多,主要是两点,一是要技术过硬,二是要八字过硬。”这是侯媛微博里置顶的段子,对于毛发医生而言,“八字过硬”不是段子,但需要随着更多好医生的成长与加入,成为“段子”。
 关注
关注
 北晚在线
北晚在线
 管理员
管理员
 2022-11-22 15:13
2022-11-22 15:13